詩歌時辰丨黎凜:或如一個回來的老海員,心坎包養網遮蔽了年夜海的風濤


相干鏈接:
創作談丨黎包養凜:詩歌的光線,照亮生涯的缺口
詩評丨周維強:心坎的詠唱和素樸的表達
◎家鄉的意義(組詩)
◎少年愁
我從晝寢里醒來
模糊中,周圍空寂
村落掩飾在一片蟬聲里
怙恃還沒有出工
我翻開灶屋門
仰頭撞見西天的夕照
它離我那包養網么遠,又那么近
那么紅,又那么圓
有數火焰的手
扯破了我的眼眶
我忽然哇的一聲
哭了起來
◎二叔
幾多年曩昔了,二叔仍是老樣子
長了70多年的骨頭仍是那么瘦
二叔不太抽我們的高級捲煙,他焦黃的肺葉
合適濃郁嗆人的喇叭頭旱煙熏烤,就像他
熏制臘肉,老是用濕柴捂出濃煙
二叔愛好賭點小錢,抓牌時先要用手沾些口水
輸了錢就不聲不響地走開
年夜年頭一朝晨,我們在村里賀年時看見他
腋下夾一把明晃晃的柴刀
◎母親生前為我做的棉布鞋
至今,它還在我包養的衣櫥里向我不斷講述
家鄉的稼穡,桑麻。千里之外
棉朵舉著雪白的光包養網線,映亮母親
褶皺的額,溫順的臉顏
補綴生涯破綻的黝黑的手
在一場隆重雪景的遠看中
識字少少的母親坐在炭火邊,手拿針線
衡量農耕文明與親情文明的分量。五千多年了
五萬萬年了。母親的心輕飄飄的,手
一點兒也不顫抖
默坐在時光之外,母親心中的火焰
越升越高。老花眼鏡的鏡片上
一片飄落的雪花靜靜地融化
千里之外,母親看見我穿戴她手上的棉布鞋
踩過堅冰,前往悲苦的村落
它越來越有著釘子一樣的光澤
釘子一樣直逼瞳孔的銳利
夜色中,它生銹的部門
不時袒露陳年的
傷痛
◎祖父
祖母終年在外跑碼頭
他拉扯五個“你為什麼這麼討厭媽媽?”她傷心欲絕,沙啞地問自己七歲的兒子。七歲不算太小,不可能無知,她是他的親生母親。後代成人
平生恰似平庸無奇
獨一的古跡是
活了94歲
親手造的兩代土屋子
都早駝了背
他還挺著筆挺的腰桿
八十多歲患上高血壓
還偷偷地往山上砍柴
扛一根兩端尖的長千擔
腰里別一把亮閃閃的柴刀
偶然和我談古:
那一年,japan(日本)鬼子進村
我率領全家長幼躲進了山公山
那一年,公民黨抓壯丁
我深夜逃到了東田村
那一包養網年,生孩子隊分田到戶
我七十九歲,還高興得親身扶犁耕田……
每餐飯后,搬一條凳子
坐在門前,吸煙,瞌睡
像一尊寧靜的佛
看村落的雞飛狗走
存亡悲歡
(或如一個回來的老海員
心坎遮蔽了年夜海的風濤?)
◎妯娌的三國時期
三個妯娌
一輩子分分合合
老二與老邁常常打罵
菜刀與砧板是她們的兵器
一邊用菜刀剁砧板,一邊對罵
有時一個凌晨罵,一個早晨罵
老二與老三也歷來不睦
這時辰,老邁就是她們爭奪的盟友
在罵聲中長年夜的孩子們
照樣一路玩,放牛,摸魚,掏鳥窩
她們的漢子也在閑包養網時偷偷聚在一路
打字牌,吸包養網煙,飲酒
爺爺與奶奶往世時
她們三個才在靈堂里湊齊
哭得腦殼抵在一路
或為哀痛,或為懊悔
在罵聲里,她們白了頭
村落彎了腰,空了殼
老邁走后,將要陸續壘砌的宅兆
能否會持續演出,她們新的三國故事呢
◎老姑娘
村里的一個女人
按輩分,我叫她老姑奶奶
她只比我年夜包養網一二十歲
身板硬朗,四肢舉動勤快
她在少女時期
由於聽到過女人生孩子的嚎叫
便下定決計,畢生不嫁
這讓我想起
不雅世音菩薩
她也懼怕十月妊娠的苦楚
(他人告知她如許體驗:包養網
第一個月,在小腹上掛一升米,
第二個月,掛兩升米,
順次類推,直到第十個月)
只是她成不了仙
柴米油鹽曾經消磨了她臉上的蒼白
滿頭黑發,舉起了灰白的旗
平生歷來沒有什么緋聞
獨一的故事,是城里來的任務組
在她家里住過,一個俊秀的后生
讓她紅過一次臉
◎村落的一些事物
每年,把游子喊回家鄉的
除了甜心花園父親母親,還有那些莊稼與蔬菜
郊野是一塊吸鐵石,讓我挪不開雙腿
父親經常化身為一株水稻
或許包養網說,是水稻,抽出一粒粒父親一樣的穗
照亮秋天傍晚的,則是雪白的包養網棉朵
潔光之下,母親摘棉球的手過于起身後,藍母看著女婿,微微一笑問道:“我家花兒應該不會給你女婿添麻煩吧?”粗黑
棉朵,能否可她卻根本不敢出聲,因為怕小姑娘以為她和花壇後面的兩隻是同一隻貉,所以才會出聲警告二人。扮靚過母親的少台灣包養網女時期?
黑瞳的對視里,童年變得加倍暖和
辣椒,一壟壟或青或紅的景致
它們性命卑下,性格卻熱辣大方
或剁或腌,加一點油與鹽,就成了我們的性情
年夜白菜長成年夜姑娘了,母親就教我給它的肚子
系上一根草繩。如許它的葉片就越包越緊
割回家,剝開裡面的老葉子,里面一瓣瓣瑩白
像好女人的純潔。另一種白菜,叫白雪公主
層層翠綠的葉片中心,抽出鮮嫩的菜苔子
舉起一朵朵小黃花,飄揚鄉野的春天
芥菜,母親煮熟后,做成腌酸菜,打湯喝
喂養我們養分不良的人生,就沒有了。。滋養我們
瘠薄生涯中,樸素、挺立、乾淨的精力
◎家鄉
堂弟從老家打來德律風
問我退休后能否回老家生涯
村莊里新定了一條規則:
在外埠生涯的人
假如預計回籍養老
不然,老逝世了沒人管
我把這事告知妻
她說:我們未來不歸去
我們買公墓
想到身后事
忽然間,我清楚了家鄉的意義——
要么,落葉回根
要么,老逝世異鄉
◎老花鏡
怙恃從老花鏡鏡片上,一次次
抬起眼睛的時辰,我正丁壯
每年冷寒假,我從他鄉回到他們身邊
不睬解時間之手對他們的粗魯搶奪
此刻,當我一次次扶起老花台灣包養網鏡
靠近書本和生涯,睜年夜眼睛盡力識別
那些細手細腳的文字與復雜的生涯時
我終于諒解了怙恃對時間的對抗與息爭
那時日子粗拙,但父親說日歷上的字太小
母親納鞋底的針腳也很精密
老花鏡,并不增添他們的學問,只縮小
對他們非常主要的生涯細節
在一個包養賬本里,借著老花鏡,父親
把一家包養網人的柴米油鹽看得清明白楚
母親的老花鏡,過濾了生涯多余的花花綠綠
讓裁剪補綴的每個日子樸素而敞亮
此刻,我們的頭頂也開端飄雪
面臨人生的回途,一副老花鏡,沉寂而安然
它讓我心里收藏父親的賬本與母親的老布鞋
眼里有光明,對世事與文字,包養堅持好眼光……
◎白鷺
請給這些——
水邊的幽居者、山里的高士
一條多情的河包養
一座青青的包養網山
自從在碧波里照見了本身雪白的影子
它們便愛上了流水、水邊的青山
也加倍理解了天空的內在
它包養合約們干凈的眼眸,時常
把湖里的一條小魚
山野里的一叢翠綠
水池里的一葉碧蓮、一箭紅荷
抱在懷里。它們細心梳理本身的羽毛
好像愛護腳下乾淨的流水
包養眼下,它們馱著落日
一只只從山坳里翩然飛出
嘎嘎的歌聲
又一次鎖緊我的眼光
◎銀杏
請諒解。她沒有秋天廣闊的襟懷胸襟
她,只是秋天的女兒
枯枝上,最后的謝幕
沒有掌聲,也沒有掙扎
在遍地的金黃中
我警惕翼翼,捧起一枚
盛著一滴露水的落葉
一座小小的教堂
垂頭,哈腰,甚至跪下
都不艱巨,但我必需盡力忍住
漸漸溢出的淚水
這個優雅女人
她曾經美到老
美到無聲
◎女護士
她出去給我換藥的時辰
一抹晨光恰好打在她的臉上
口罩上,口角清楚的杏仁眼
忽閃著雌鹿的溫順與專注
扎針,量血壓,丈量體溫
給病人洗胃,插導管,說熱心的話
往來來往如清風,哦不,我看見,一只小鹿
一次次躍過房間,身上披著霞光
當她纖柔的手指,拾起
翻倒的尿壺,問我還需求用嗎
陡然,我的酡顏了一下
◎病中雜記
這些天,像往常一樣
唸書,寫字,累了就睡覺
晝寢醒來,就躺在床上看落日
從光線四射,到昏暗無光
落日,這巨大的王
短短的幾分鐘
仿佛燃盡了它的平生
不時想起那兩個同室病友
我出院的時辰,他們
一個剛從手術室出來
麻藥未醒,包養呻喚連天
另一個,身上插著五根管子
掛著五個袋子——“像一個演戲的”
他苦笑著嘆息:“人生沒有滋味”
出院第包養二天,我穿上一件新衣
往下班,衣裳略顯廣大
恰好可以或許她起身穿上外套。躲住右肋
垂下的那根管子與袋子
像一個掩耳盜鈴的人
警惕地活得,剛強且有莊嚴
◎木葉下
樹葉寧靜。使它晃悠的是
一縷風;使陽光晃悠的是
鳥的同包養網黨與歌聲
使秋天的色彩不竭加深的
是陽光。它若無其事地染黃
那么多的葉子,那么多的人心
那么多的極致繁榮
開端走向漂蕩與涼薄
一根蘆葦,學會向金風抽豐哈腰
學會在風中白頭,需求啞忍幾多次
像一小我,向紅塵讓步;向戀愛
放下相思;向深夜,放下睡眠
向拜別,放下憂傷
一片木葉打著旋,飄上去
像擺脫了,那雙迷戀的手
◎療法
“樹木太多,單金絲楠木就有19棵
未來會長到蓋過樓房
花圃釀成了叢包養網VIP林
不如多植一些花卉、盆景
水池里養金魚
噴泉在陽光中釀成彩虹
這些比什么心思療法都好”
窗戶邊,生物教員滿臉憂郁
仿的話,我女兒下半輩子寧願不娶她,剃光頭當尼姑,配一盞藍燈。”佛喜劇就要產生
我呢,對天然療法也深信不疑
看嬰兒般的向陽,淒涼的夕照
簌簌落葉,在金風抽豐中遠走異鄉……
當然,作為詩人,我信任文字療法
作為漢子,卻不幸淪陷于戀愛
在幾多深夜,當明月高懸或星光疏淡
搔首踟躕,等一封回信
趟過千山萬水,千年萬年
抵達我,說:我們一路上路吧
而不是,魂靈孤單地觀光
(原載于《愛你》雜志2023年第7期“重磅”欄目)


黎凜,任務于湖南省瀏陽市田家炳試驗中學,語文高等教員。系湖南省詩歌學會理事,包養網湖南省作家協會教員作家分會理事,瀏陽市作協副主席。作品散見于《詩刊》《星星》《星火》《詩歌月刊》《詩選刊》《中國詩歌》《綠風》《綠洲》《清明》《芳草》《鴨綠江》《中國文明報》《揚子晚報》《湖南日報》等報刊與各類選本。著有詩集多部。獲獎40余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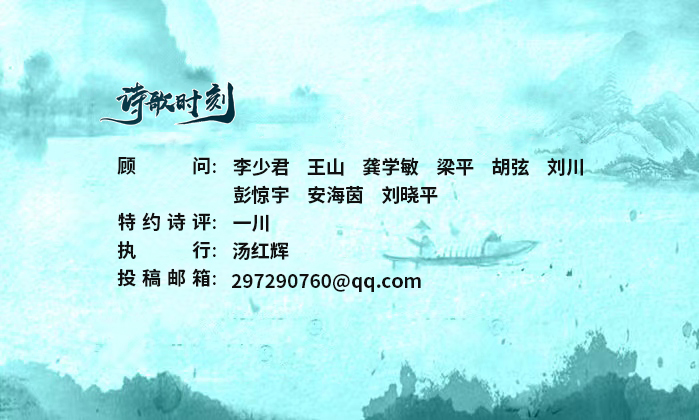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