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儒賓】體用相待的本聊包養心得體論——道體論儒者的選擇
體用相待的本體論——道體論儒者的選擇
作者:楊儒賓
來源:《新經學》(第十輯),鄧秉元主編,上海國民出書社 2022 年 12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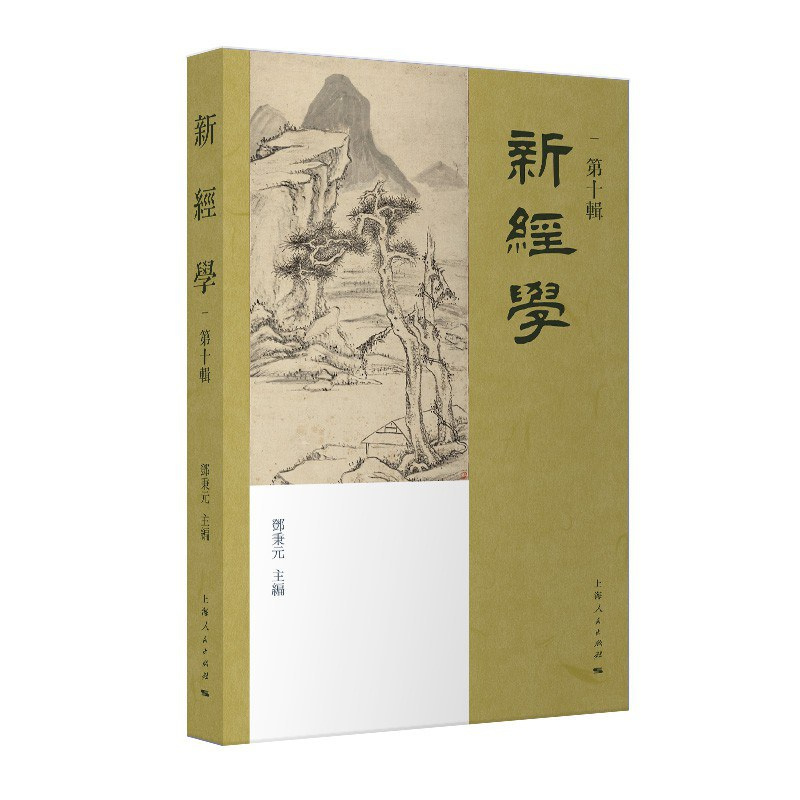
作者簡介:楊儒賓,男,1956年生。臺灣年夜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臺灣新竹清華年夜學哲學研討所講座傳授。重要研討領域為先秦哲學、宋明理學、東亞儒學等。著作有《儒家身體觀》《異議的意義:晚世東亞的反理學思潮包養網站》《從〈五經〉到〈新五經〉》《1949禮贊》《儒門內的莊子》;編著有《中國現代思惟中的氣論及身體觀》《儒學的氣論與功夫論》《東亞的靜坐傳統》《天然概念史論》《中國哲學研討的身體維度》等書;譯有《東洋冥想的心思學:從易經到禪》《孔子的樂論》《冥契主義與哲學》《宇宙與歷史:永恒回歸的神話》等書。
一、 媒介:“本體”與“形上學”的詞匯之義
“本體”一詞是中國哲學的老詞匯,理學在十一世紀興起后,理學家用到本體、體用、本體—功夫的詞匯頗多,本體論的思慮可視為理學的最基礎的思維形式。但本日哲學界應用的“本體論”一詞乃來自西洋哲學的ontology的翻譯,並且很能夠是經由日譯漢字的管道,再經由japan(日本)傳到中國[1]。ontology在西洋哲學的脈絡底本探討萬物存在的學問,此用語和理學傳統中所用的“本體”一詞,頗有相涉之處,理學家所說的本體之義確實也探討了萬物存在的基礎。“萬物”乃現實存在的總稱,存期近有,ontology是以有了另一個名為“存有論”的中文兼顧。相對于釋教重空,道家重無,儒家則重“有”,從儒家的觀點看,“存有論”此譯語亦有佳處。
“本體”或ontology此詞當然有探討萬物之有之義,它的性質能夠隸屬天然哲學,也能夠隸屬于神學的范圍。但在理學的脈絡中,它不克不及脫離生命之學的格式,總會含攝心性轉化的內涵,它常和功用(用)或功夫連用。如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2];或言“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3],這是熊十力的名言,我們在理學圈子不時可以看到類似的語言。至于“本體—功夫”連用中的“本體”更可說是功夫論的語言,它常被視為功夫的依據。“功夫論”一詞意指一種以天道生命相貫通為理論主軸,并思求轉化現實的身心以契進超出境界的品德實踐之學問。由于理學的品德實踐性情使然,本體總和轉化身心的實踐連結在一路,“本體”一詞凡是預設了“本體的顯現”之潛臺詞。
論及“本體的顯現”,在理學的脈絡中,甚至在六朝后的三教傳統中,我們很不難想到一種作為宇宙現象基礎的宇宙心形式,我們可稱作心學形式。“心學”之“心”的名稱依各教的用法而互異,它可稱作如來躲自性清凈心,或本意天良,或道心,其心的內涵也依各教教義分歧,天然差異顯著。但是,此心作為現象基礎且彰顯現象存在的效能卻是分歧的,釋教真常唯心系的“如來躲自性清凈心”最為明顯。華嚴宗可說是“如來躲自性清凈心”此概念最徹底的展現,浩浩華嚴義海無異于“如來躲自性清凈心”一詞的剖析命題,一切由此法界流,一切還歸此法界,本意天良在全體現象中蔓衍展現。
但是,“本體”當然是實踐的概念,“本體”意味著“本體的顯現”,它依賴于學者現實的身心狀態之轉化,人心化為道心,其內涵乃克實現。但是,本體的實踐性情有賴于主體的參與是一回事,“本體的顯現”能否便是本意天良的朗現?兩者能否可以畫上等號?這是另一回事,此事牽涉到理學系統內部爭議“心與理的關系”此年夜議題。如持“心”、“理”統一內涵者,其本體即落在心上顯,本體即心體。反之,如落在“性”上顯,其本體即為性體。如落在“道”上顯,其本體即為道體。雖然是統一個“本體”概念,落在主體詞語“心”,落在個體性詞語“性”,落在宇宙論詞語“道”上看,其格式即會年夜為分歧。
作為理學第三系的道體論者也有玄秘的心性之學[4],但道體論者不是心體論者,它的重點放在天然全體生生不息的道體上解釋。“本體的顯現”這個語詞的“顯”字是道體論者喜歡用的詞匯,而他們所以要用這個詞匯,是有哲學的意義的。道體論者的理論對手是佛、老,佛、老思惟的焦點概念一在空,一在無。釋教說“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5]。老子說:“全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6]引文中的“空”、“無”皆有一切法皆空,全國萬物天性皆無之意。兩教的“空”、“無”天然已不是字詞的文字意義所能拘囿的,兩者不會是斷滅空、斷滅無之謂,它們總有創造性的空或創造性的無之內涵。但從道體論者的觀點來看,佛、道兩教從空、無出發,若何出現天然世界之旺盛,某人文世界之豐饒,總費思慮,難得其解。道體論儒者不從空、無出發,而是從天,從道,從一種帶有實在論內涵的氣之概念出發,從氣之離合分合著眼,由此解釋世界的天生變化。
從一種形而上意義的氣之觀點進手,世界的各種變化,包括存在樣態最為劇烈的有無存亡都不是存在與虛無之間的斷裂,而是顯隱之間的變化,世界的存期近是氣的變化的歷程。道體論者的道體以氣化為具體內涵,但是,天然氣化究竟是物質變化的歷程,還是還有一種非人的意志所及的六合之心的神圣意志的內涵?此事乃是本日中國哲學史家論氣化論者的思惟特點時,喋喋包養留言板爭議不休的焦點。但是,道體論者詮釋他們本身的論點時,顯然主張包養軟體道體是本體的展現,它有更高的精力內涵,道體之由幽而顯,也就是它的自我展現,乃是“道體”一詞該有的內涵。
由“本體”預設了“本體的顯現”一詞,我們可以懂得牟宗三論理學著作時常用的“本體宇宙論”一詞。由于在西洋哲學傳統,本體論(ontology)凡是是論存有(being)的學問,而宇宙論(cosmology)則是論世界變化天生(becoming)的學問,兩者的關懷重點分歧。牟師長教師混雜而一之,依本日的哲學用語,難免會惹起爭議。但是,在理學系統中,其本體之義確實具有作為萬物之體,且生生不息之義,亦即理學的“本體”不是存有而不活動的實體,它當作為動詞用,它是作為萬物依據的生生不息者,本體永遠在氣化的創造當中。這種既作為本體且作為運動者的本體義乃本文所說的第三系理學的典範敘述,它跨越了本體論,也跨越了宇宙論的領域。本體宇宙論一詞如放在理學的脈絡下懂得,并不是錯誤的用法,本文也采用了牟師長教師的用法。
“本體宇宙論”一詞和本日學界所用的“形上學”一詞的內涵幾乎重疊了,本日哲學用語的形上學凡是即包括宇宙論與本體論兩個子目。在中國的思惟傳統中,“形上學”一詞出自《易經·系辭上》“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在《易經》的原始用法中,“形而上”并不是作為一種知識領域的概念躍上學問舞臺的,它是與“形而下”連用,作為描繪道—器這組主要術語的狀詞。“形而上”變成了本日哲學學門主要的知識分支“形而上學”,乃源于近代中國的知識重組時期的metaphysics之譯語所致。中國原有的三教系統中與西洋哲學的本體論、宇宙論相關的知識領域并非沒有,玄學、義學、內學、義理之學、心性之學、道論如此,都有近似之處。但在二十世紀的譯語競賽中,來自《易經》的“形而上”一詞畢竟勝出了,它成了metaphysics在東方漢字世界的化身——形而上學。
雖然本日學界應用的“形上學”一詞的實質內涵,源自東方,但此化身既然應用了漢字,它就不成能不受漢字的影響。語言是思惟的器官,漢字與漢語思維密不成分,“形上學”此一新興語匯竟然可以打敗眾多陳舊的家族語匯,脫穎而出,其過程牽涉到本日漢字世界對形上思維的懂得。此詞語負載了中西兩組主要知識概念在歷史的相會,犬牙交錯,文明含量極濃。簡單地說,“形上”一詞不論中東方,都有對物之世界更高一層的反思之義,但來自西洋哲學的metaphysics乃是對“天然之學”(physics)的后設反思之學,它可謂后天然之學(meta-physics),中土的形上學則意味著“后身心之學”(metaphysiopsychology)[7],更恰當地說,乃是“后身心天然之學”(metaphysiopschophysics),它來自現實狀態(身、心、天然)轉化后所呈現的境界。“形而上學”與metaphysics兩個詞語之間的演變對勘,有能夠可以揭開中西交通過程中被掩蓋或新增添的義理。
本文探討理學第三系的本體論。本文應用的“本體論”、“形上學”基礎上是源自行處理學的用法,它們都是傳統所說的生命之學范圍內的概念,語詞的內涵預設了語詞的朗現,也就是都有轉化身心的實踐請求。牟宗三師長教師所說的本體宇宙論的內涵也當放在這樣的脈絡下對待,即存有即活動的本體是第三系理學的“形而上”一詞的特別內涵。本文標題“體用相待”和理學文獻中常見的“體用一如”、“即體即用”、“體用不分”如此,內容頗有交涉處,但傳統理學應用的這些語匯還是難免統一性的性情太強,圓融義壓倒了需要的張力,體用之間的緊張關系被淡化了。氣化之生生不息,也就是“用”所帶來的新新、衝破、斷裂之義不難遮蔽不彰,道體論的殊勝因此也就不難被淡化。本文假借《老子》“相”的語式[8],用以凸顯道體論者的本體乃“世界安身于本體—本體之用乃既屬本體而又非本體一切—本體之用復反哺于本體”的詭譎構造。
二、圣人本天:與唯物包養心得論形式的對勘
作為理學第三系的道體論的哲學出發點年夜分歧于心體論者及性體論者,在于后兩者的主體哲學的性情是基礎的,轉化身心的功夫論是學問的重心,本體論的問題融解于功夫論或境界論的格式中。相對之下,道體論者的思慮不是從主體出發,而是從“天”,也可以說從主體與天道的關系出發,主體的轉化與天道的證成劃一關心,但“天”或“天道”的證成是道體論哲學的主軸。轉化現實身心以盡心知性的功夫論當然也是此學要義,但它的內涵是要在“天”的總貿格式下尋求定位的。
“天”是中國文明的長久詞匯,在商周時期,“天”即有人格神的天主之義,在存有的次序中,天占有最高的位階。在三代之后,特別強調“天”在存有次序的最高位階,祂是創造及價值的終極來源之思惟可謂無代無之。天的權威在平易近間當然始終不曾失落落,在儒學史上,漢代思惟的主軸更可以說是以天為中間,是種“本天”的哲學。這套以天為中間的哲學在經學意義上,便是以陰陽氣化為內涵的宇宙論;在政治上,便是以天人感應為運作機制的政管理論;在倫理或品德上,便是以“人副天數”為本的法天哲學。
漢代“本天”的陰陽氣化宇宙論在本日的學界并沒有獲得太好的評價,即便商周的天道論的價值也一樣遭到忽視。這些以天為本的思惟所以在現代中國備受忽視,當然和平易近國來的反宗教思潮、唯物論年夜興以及主體性哲學的發達等等相殺相生的思潮之匯流有關。但是,我們假如從“太始存有論”的觀點著眼,商周的天道論所提醒出的天乃在天然的“圣顯”(hierophany),天道透過陰陽、氣化、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分布,它在年夜天然顯現它的圣功之偉業,其說年夜有勝義,我們可以看到三代天道論與宋明道體論的隔代唱和。
三代天道論與宋明道體論之關系若何懂得,這是個年夜問題。但無能否認地,法天的倫理主張或以陰陽氣化為焦點的宇宙論思惟在理學升起的階段,可以找到類似的痕跡,並且是頗類似的構造。《宋史·道學傳》論理學的來源時,包養網推薦先抨擊孟子之后的儒學傳統,指責歷經漢唐諸代的演變,儒家思惟要旨皆不得其傳之后,此傳接著說:
千有余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于舂陵,乃得圣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年夜原出于天者,灼但是無疑焉。[9]
《道學傳》勾畫了周敦頤與張載之學的大體后,又將邵雍列于張載之后,三人似可視為統一系統,因為這三人都主張“道之年夜原出于天”。至于此傳又將二程、朱子、張栻也放進往,同樣視為《道學傳》中人物,乃因《宋史》所說的“道學”即為后世所說的理學,其所列名單較為廣泛,可成一說。但我們如從更內部的思惟類型考量,拿周、張、邵三子的思惟作為檢證的標準,或許可再加上同時代的程顥(明道),四人可以說都主張“道之年夜原出于天”,他們都有本天,也就是本體宇宙論的思惟。
四人當中,程顥和程頤往往并稱,后世儒者也常將他們兩人一體對待,籠統地稱作程子。但依當代中國哲學史家馮友蘭及牟宗三的判斷,二程思惟并分歧系。二程兩人思惟之異同是個復雜的問題,但在本體論上,我們有來由將二程分開,程頤是性體論者,程顥則可歸宗于主張“道之年夜原出于天”的道體論一系。程頤有一名言:“圣人本天,釋氏本意天良。”[10]此句話雖出自程頤,但如移之于程顥,能夠更為恰當。大略道體論儒者對于心學的主張皆有極年夜的警戒,北宋理學家這般,晚明的王夫之、方以智也是這般。
程子以“本天”、“本意天良”分判儒佛,他的這組語言是有決定性的語言。程顥體道甚深,人格如渾金璞玉,語言溫潤流轉,修養等級接近化境,是以其思惟性情不易把握。但是,假如我們能正視“本天”的焦點義,程顥思惟的焦點樹立在天道此焦點義上,不難看出來。好比這段話: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正人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任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11]
這段語言是典範的程顥宗風,渾淪圓融,處處一也,一也。但是,程顥明言功夫的條件乃是“正人當終日對越在天”,全文的主詞是“天”,“其體”、“其理”、“其用”、“其命”的“其”字都指“天”而言,它的理、用、命的屬性由此展開。
程顥的思惟和人格皆極渾融謙沖,如太和元氣風行,是以,不易看出他的思惟屬性。但是,我們如仔細剖析他的焦點思惟地點的天理、天道論,牟宗三的《心體與性體》已幫我們作了極好的歸類[12],程顥討論“天理”、“天道”的文獻已被他合為一編。我們不難發現這兩個章節所列的文字都是從客觀的天道、天理立論,其天道、天理皆被視為“天”之道遍化于全國萬物,天之理也廣泛地凝著于全國萬物,程顥早就說了:“終日乾乾,正人當終日對越在天。”我們不會忘了周敦頤《通書》的名言說:“圣希天,賢希圣,士希賢。”我們也不會忘了張載的主張:“年夜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圣人。”若此之言,皆可為《宋史·道學傳》所說的“道之年夜原出于天”者張目。
但是,圣人本天,“天”意云何?在漢代風行的倫理主張中,本天之說也是可以說的。漢儒的天充滿了奧秘的旨趣,天意當然深躲于不成測的年夜化深淵,但它有時會透過天然的表現,或禎祥,或災變,而顯現出來。所以人與上天的共同、效法,即成了主要的倫理表現。漢儒奧秘的天人感應說可以視為商代之前巫風習習之下的天帝觀的返祖重現,那是個以內在的天意吞噬主體判斷的準宗教。顯然,道體論者所說的“天”不會是那種充滿奧秘氣息的陰陽災異之天。
除了至高神的天與陰陽災異的天之外,“天”在北宋之前,也有天然義,郭象所說的“天也者,萬物之總稱也”。天是“萬物”之外或之上的超出者?或是萬物之總稱?道體論者引來的爭議之焦點在此。在廢除天的奧秘性且具哲學理論高度者,郭象當是魏晉時期數一數二的愚人。在郭象現象論的世界圖像中,天(天主)已從世界退卻,蒼天已逝世,萬物皆自生獨化,萬物之所以為萬物乃因物在氣化風行之年夜流中,自凝自固,忽爾獨化,物決定了本身的存在。郭象從除魅化后的萬物或天然的觀點下所看到的天,乃是氣化變動不已的內涵。
道體論者都有氣化之道的主張,宇宙的生化離不開氣化的過程,此義乃道體論者的共法。但在北宋之前,“氣”的概念常和天然或物結合,氣被視為構成天然或任何物的構成因。在“萬物由氣組成”的思維形式下,“唯氣”之說的哲學常被劃歸到唯物論的陣營,一九四九年之前已是這般;一九四九年之后更是這般。在筆者所說的道體論愚人當中,王夫之被視為唯物論者的聲響尤年夜,甚至新儒家的牟宗三師長教師也頗游移,他有時認為王夫之的哲學不克不及往下拖,成了唯氣論,但有時又覺得他的唯物論的嫌疑極濃[13]。牟師長教師對王夫之的哲學性情之詮釋游移不定。所以他除了在歷史哲學處會論及其人其學外,對王夫之的天道生命說年夜體以緘默帶過[14]。
張載在當代中國哲學史家的研討中,也常被視為唯物論儒者,短期包養並且是極主要的代表,這種詮釋觀點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年夜陸學界,更為廣泛。即便進進二十世紀八十年月以后,政治的壓力已減,馮友蘭重寫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時,仍堅持張載是位唯物主義哲學家,並且是理學傳統中唯物主義路線的代表。由于張載是王夫之平生瓣噴鼻不斷的愚人,王夫之將張載視為本身哲學的祖型,所以我們無妨即以張載、王夫之兩人為例,檢討道統論者的法上帝張若何在奧秘的天意與除魅的唯物論之間晃動,詮釋的性情六合懸隔。
馮友蘭的唯物論解釋基礎上是按照張載唯氣論之說而來,張載的《正蒙》是部體系相對完全的著作,在理學傳統中,這般客觀論述的體系性著作相對較少。《正蒙》一書中,論氣為萬物構成的詞句不少,《正蒙·太和》云: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起落、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緼、相蕩、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年夜堅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成象為神。不如野馬、絪緼,缺乏謂之太和。
“太和”一詞出自《易經》“保合太和,乃利貞”。張載借用此語,用以描寫一種宇宙整體和諧的狀態,但張載的用法將“太和”一詞由狀詞轉為名詞。“太和”像京都學派所說的“場”,一切存在的變化皆在此場中發生。
假如我們再剖析“太和”的概念,即可發現太和的實質內涵是彌漫氣的存在,氣是構成存在的基礎,氣化風行,中涵各種感應相蕩的性質,這就是所謂的“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張載的文字有時頗澀,此句話的意思當是說太虛的實質內涵便是氣,它離合于太虛的場域,聚則成物,散則成氣,“氣聚則離明而無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類似的這種語言,我們在戰國秦漢的子書不時可以看到。假如先秦時期的這些語言所描寫的氣之離合的語言是唯物論,那么,張載以氣之離合解釋物之離合,氣被視為“一種極細微的物質”,我們沒有來由不認為張載是位唯物主義的愚人。
道體論愚人的哲學基礎性情是典範的中國三教形式的天道生命之說,但常會被視為唯物論者,張載這般,王夫之更是這般。王夫之唯物論的標簽被貼得很緊,應該是無風不起浪。底下這段話是他對《易傳》一段注釋,很是有名,不少探討王夫之的文章都提過這則注釋。但筆者認為這則注釋的語義其實相當曖昧,解釋可以天壤懸殊。關于王夫之哲學的唯物論解讀公道與否,我們無妨就從此則文字談起:
全國惟器罷了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成謂之道之器也。……無其器則無其道,人鮮能言之,而固其誠然者也。洪荒無揖讓之道,唐、虞無吊伐之道,漢、唐無本日之道,則本日無他年之道者多矣。未有弓矢而無射道,未有車馬而無御道,未有牢醴璧幣、鐘磬管弦而無禮樂之道。則未有子而無父道,未有弟而無兄道,道之可有並且無者多矣。故無其器則無其道,誠然之言也,而人特未之察耳。
形而上者,非無形之謂。既無形矣,無形而后無形而上。無形之上,亙古今,通萬變,窮天窮地,窮人窮物,皆所未有者也。故曰:“惟圣人然后可以踐形。”踐其下,非踐其上也。……器而后無形,形而后有上。無形無下,人所言也。無形無上,顯然易見之理,而邪說者淫曼以衍之而不知慚,則正人之所深鑒其愚而惡其妄也。[15]
引文出自王夫之對《易經》名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解讀,此一注解不成能不是了義的文字,其解釋力道遠超越王夫之其他的文字之上。注文絕不含混地宣稱“形而后有上”、“無形而后無形之上”,本文認為我們可逕予稱呼注文持的是“形的形上學”,“形”比“形上”享有存有論的優越地位。
引文破題處,王夫之即便用了“全國”這樣的普世語匯。“普世”一詞常用于政治領域,它意指一種超出于任何特定的觀點上的視野,任何觀點假如囿于一時的、特定國族、語言、風俗的論述,即非普世的。普世的語匯也見于中國傳統的哲學論述,類似“全國惟X”的語式在佛學、理學中相當常見,X這個符號凡是指的是生命之學的語匯,如“盈六合間皆心也”、“萬法惟識”,或介于心物之間的“惟氣”之論,如“盈六合間皆氣也”。王夫之能夠是包養管道較早應用“惟器”一語的先行者,王夫之不單說“惟器”,並且對道、器的關系作了與傳統解釋年夜相逕庭的一百八十度的年夜回轉,“未有弓矢而無射道,未有車馬而無御道”,這類的話語說得相當明白,“道”顯然是由“器”導引出來的,道是器之道,器不是道之器,器在時間及本體論意義上都有它的優先性。“形而上”變成是附屬在“形”上的后添物,最多是缺乏以自立的屬性,“形”才是概念的主體。王夫之這段話會遭到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國哲學史家的重視,不難懂得;相反地,像牟宗三師長教師這些新儒家學者會居心忽視之,其來由也不難想象而知。
我們假如對王夫之這段“形而上”注解作唯物論的解釋,至多文理通暢,足以成說。他的論點所以會惹人注視,重要是他的論點似乎太異類了,太偏離思惟史的主軸。很明顯地,他的立論是有明確的針砭對象的。起首,便是正統經學的解釋:
道是無體之名,形是有質之稱。凡有從無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謂之道也,自形內而下者謂之器也。[16]
上述引文出自孔穎達的《周易正義》,其注語和王夫之所說,剛好南轅北轍,並且幾乎無一不反。孔穎達的注疏從唐代后代表官方版的權威觀點,是科舉考試的標準謎底。從“有從無而生”、“道在形之上”等等語言看來,它無疑反應了魏晉以下的玄學觀點。“形而上”一詞在玄學家眼中,常和“無”字結合并論,何晏的觀點是典範的例證,孔穎達的注釋也頗有“貴無”說的形姿[17]。在《易經》學的范圍內,北宋之前,正統的注本明顯地指出“無”乃形而上者,形上之道的本質便是“無”。王夫之嫻熟經學,他以“六經責我開生面”自許,他對形上—形下關系的解釋假如沒無力反前代主流經學的觀點,這是難以想象的。
“有無”、“道器”、“理氣”先后的問題不單見于漢唐經學著作,類似的爭辯在王夫之之前的理學內部也已充足討論過,重要甜心寶貝包養網的爭鋒之一是圍繞著周敦頤《太極圖說》的“無極而太極”一語若何解釋,朱子和陸九淵曾重複討論。陸九淵反對《太極圖說》的說法,認為周敦頤的論點其實只是老子“有生于無”的盜窟版,是以儒家之名而遮蔽道家之實[18]。“有”、“無”先后的問題除了是存有論的問題外,也很不難牽涉到品德哲學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張載生前即已出現。在王夫之生前,有無之說與品德善惡的問題更已被充足地討論,此中一個爭鋒的岑嶺期是陽明后學、東林學派針對“無善無惡”之說的重複辯論。這兩場爭辯的理論價值極高,其內涵都深刻到本體論與功夫論極細部的問題,並且多與學者在性天交合處的體悟有關。滋事牽涉頗廣,且論者已多,本文在此僅簡要指出,以作為王夫之顛倒道/器、形上/形下關系的佈景。
“有”、“無”能否必定牴觸,其實在理論上紛歧定那么難以解決。事實上,也頗有理學家認為“無”或“無極”可以拉升到“有”或“太極”的層次。但是,由于理學家對“有”在本體論上的優先性一貫很堅持,所以對于“無”的語感一貫欠安,甚至認為無法思慮,他們不不難允許此詞語在形上的世界可以升至“有”的層次。在許多明儒(包括王夫之自己)的眼中,道家主張宇宙的來源與根據皆為“無”。王夫之明顯地反對以“無”解釋“形而上”,他繼承張載“有”的哲學而來。不單繼承,他更焦點化地將“有—無”、“形上—形下”的關系顛倒了過來。而“有”的敘述觀點中,王夫之也和張載一樣,選擇“氣”作為首出的詮釋原則。
論及“氣”即很難不論“理”,“理”、“氣”是一組相對而起的概念。王夫之“形上—形下”、“道—器”關系的唯物論解讀可所sd包養以很體系的,與“形上—形下”、“道—器”組語概念很接近的便是理—氣關系。在前代尤其是程朱理學的體系中,理先氣后、理形上氣形下之說常居主流,王夫之始終反對這樣的理氣關系,他說:“言心言性,言天言理,具必在氣上說,若無氣處則具無也……繇氣化而后理之實著,則道之名亦因以立。”[19]類似的語言在王夫之著作中不斷出現,世界的本質是氣,這個命題是貫穿王夫之思惟的一條主軸。至多從年齡以下,氣常被作為天然哲學的用語,它是種精致的物質因包養網VIP,王夫之“氣先理后”、“氣主辦從”之語不只是針對道家、佛家而言,他也針對程朱理學而發。他的理論出發點似乎可以解釋成是站在唯物論的立場上,同樣對張載“虛空皆氣”的命題作了發揮。往前溯源,先秦兩漢的元氣論主張似乎可成為王夫之之說的祖型。
從周敦頤、張載到王夫之此一系列的道體論愚人思慮天道生命的問題時,多有“本天”的主張,這是個與遙遠的天道崇敬的傳承有關的學說。但天也是萬物之總名,它是氣化歷程之總稱。由于氣的模態可用“一種極細致的物質”解釋,是以,只需氣論在其思惟體系中占有主要地位者,都難以防止“作為唯物論的唯氣論”之解釋,張載、王夫之都曾被拉到唯物論的陣營,即是以故。但是,“氣”在中國的天然敘述中,當然常被視為萬物存在的質料因,但以質料因解釋氣字,此一進路能否合適理學家本身的構想?道體論儒者“本天”的主張和“本氣”的主張連袂而至,孰是孰非?能否有更公道的解釋?
三、長在不逝世之物的品德生命
氣之一字,迷悟之門,問題的爭議還是要回到“氣”在歷史走過的足跡。
中國哲學傳統中,“氣”往往同時兼具形上與形下義,兼具精力因與質料因,這樣的現象是極明白的,所以即便支撐唯物論說的人,也發現張載、王夫之等道體論哲學家的話語時常夾有唯心論或形上學的尾巴,這些語言再若何解釋都解釋不失落。為辨別其間異同,也為了凸顯道體論儒者的思惟都有向上躍升的超出義,我們無妨以朱子的思惟作為對照,朱子是理學家當中從本質上辨別形上與形下界線最清楚的儒者。有學生問他:“先有理,抑先有氣?”朱子答覆道:
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高低言,豈無先后!理無形,氣便粗,有殘餘。[20]
上述這段話語是典範的程朱理學的解釋,程朱理學解釋“形而上”一詞,其義都指向現實存在之上的另一層超出的存在。現實的存在是“氣”,是“然”;超出“然”之上的異質的超出存在是“理”,是“所以然”。“然”是狀態詞,也是對話時回應的確定語。《莊子·應帝王》云:“栩栩然蝴蝶也。”從理學家的觀點看,道家的“然”如夢中蝴蝶,這般只這般,不克不及再有超出的確定。佛家的“然”則如蝴蝶之夢的如夢幻泡影,真諦也是真如,真如的本質便是空。程朱之“然”總是需求再上翻一層,有更高一層的異質的確定。“為什么會這般”是程朱理學的焦點關懷,但程朱的發問不是知識論的發問,而是一種存有論疑情的關懷,程朱理學認為世界不成能是偶爾的,它是“必定”。
必定是對偶爾的否認,但這種必定不是命定論,因為這種必定乃是天理下的必定,是史賓諾沙哲學意義下的必定,它毋寧是“難道命也,順受其正”的“天命”的意思,而不是萬物存在的知識之說明[21]。
有“然”即有“所以然”,程朱在本體論的地位上將“所以然”置于“然”之先,“所以然”是理之天然,理之必定,“所以然”具有獨立的位置。這些語言良多,我們且列上面這兩條: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一闔一辟謂之變。[22]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23]
程朱論及“然”與“所以然”,或理—氣的關系時,有時強調兩者的一體性,有時強調理先氣后。這種表達方法的收支并沒有牴觸,說無先后,乃是從現實世界的存在論的觀點考量。在時空世界中,從來沒有無理之氣,也沒有無氣之理,兩者無先后可言。說理先氣后,乃是從本體論的觀點著眼。在非時空的格式下,“變化”的范疇消失了,宇宙論的思慮被本體論的思慮代替了,事物構成的原因乃是本然狀態的理據的關系。依本體論的角度考量,理—氣或道—器兩者的“先后”之意義就會紛歧樣。
道體論與性體論一系思慮體用的問題時,有異有同,不克不及單方面地作整體的判斷。我們假如對照王夫之與程朱理學所說,不難發現他們都依“然—所以然”的方法思慮問題,也就是依“形—形而上”的理路定位道—器、理—氣的關系。差別當然也是很明顯的,在本體論的位階上,程朱有很強烈的後天的性理論的承諾,理(性)、氣兩者異質異層。王夫之在這點上可以看出對程朱理學相當不滿,為了凸顯形上、形下的連續性,他的語言的語式似乎將程朱理學的形上—形下關系顛倒了過來,氣在理先,理似乎是氣的述詞。說顛倒,我們很不難聯想到馬克思顛倒黑格爾世界觀的有名隱喻,事實上,這個頭足顛倒的隱喻也常被當代學者應用,借以凸顯王夫之的唯物論思惟沖破程朱意識形態的貢獻[24]。
假如我們以王夫之《周易外傳》注解《易經·系辭上》的“形而上—形而下”、“道—器”的概念為準,我們不克不及不承認:王夫之被視為唯物論者,或是反程朱理學的後天論路線,乍看之下,這種解釋是有必定的說服力的。如“太極”、“理”乃是程朱理學的焦點義,程朱視“太極”為“理”,而“理”是“形而上”者,上述這些話在程白文本里是有憑有據的。但王夫之論“太極”卻說:“‘陰陽’者太極一切之實也。……合之則為太極,分之則謂之陰陽。”[25]“陰陽”和“太極”是分合的“量”的關系,而不是質的差異,分合的關系可以解釋成“整體”與“部門的綜合”的關系,“陰陽”是代表整體的兩部門,兩者其實皆是氣,“太極”則是對陰陽實體的后設語詞。王夫之論“理”、“氣”的關系則說:“理本非一成可執之物,不成得而見;氣之條緒節文,乃理之可見者也。”[26]“理”、“氣”是語義(sense)有別而指涉(referrence)雷同的一組語匯,但“理”依靠在“氣”之上。這種理氣關系論在王廷相、吳廷翰處常見,單單看文字,可說是統一種語式的表達。這些話語都顯示王夫之重視經驗的、實證的傾向,乍看之下,居然有幾分孔德的學風,更帶有濃烈的后天型氣學的風味。
王夫之是重氣的儒者,普通而言,重氣的儒者凡是也重物、重身體、重勢、重歷史,從張載、王廷相到王夫之、戴震,莫不有此傾向。但是,重氣的哲學家能否就是主張唯物論,年夜可深究。筆者認為紛歧定,並且能夠是彌近理而年夜亂真,關鍵在“氣”的性質若何解釋。王夫之之前,張載的哲學該若何定位,也是中國哲學領域出現過的學術問題。王夫之哲學師承張載,他面臨和張載類似的哲學定位的難題。但王夫之因為下語更獨斷,他的思惟堂廡更年夜,分歧領域的知識之彼此滲透也更為緊密,是以,定位也就更麻煩。但終究說來,王夫之以張載的繼承者自居,筆者信任他并沒有誤解張載,王夫之的思惟旨趣基礎上就是關學的。張載假如不克不及冠上唯物論者的帽子,王夫之同樣也不成以。
且看下列三組資料,統一組的文字列出A、B兩項,分屬張載、王夫之兩人,這三組資料銓釋的詞目都是理學傳統中主要的形上學詞匯:
(一) 形而上:
A. 凡不形以上者,皆謂之道,惟是有無相接與形不形處知之為難。須知氣從此首,蓋為氣能一有無,無則氣天然生,是道也,是易也。[27]
B. 形而上,即所謂清通而不成象者也。器有成毀,而不成象者寓于器而升引。未嘗成,亦不成毀,器敝而道未嘗息也。[28]
(二) 生命:
A. 品德生命是長在不逝世之物也,己身則逝世,此則常在。[29]
B. 神化者,氣之離合不測之妙,但是有包養一個月跡可見;生命者,氣之健順有常之理,掌管神化而寓于神化之中,無跡可見。[30]
(三) 性:
A. 天所性者通極于道,氣之昏明缺乏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于性,遇之吉兇缺乏以戕之。[31]
B. 性者,生之理也。均是人也,則此與生具有之理,未嘗或異,故仁義禮智之理,下愚所不克不及滅……受于形而上……形而上者,亙存亡、通晝夜而常伸,事近乎神。[32]
這三組文字的A項取自張載分歧著作中的記載,B項文字都是王夫之對張載《正蒙》的注包養情婦釋,也都是對《易經》一書的定位。《易經》一書乃取材宇宙之間的變化云為、道氣化成之象而成之書,由于《易》以道陰陽,陰陽不論解作氣,或解作宇宙間的兩股相反相成之力道,整本書所顯現的世界圖像便是宇宙全體的轉化流轉,氤氳化生,一切的差異皆是統一本質的變化所致。它的風格像是古典時期的宇宙論,其性質則如劉述先師長教師詮釋黃宗羲時所謂的“內在一元論”[33]。“內在的一元論”如和天然氣化的世界觀結合在一路,萬物的變化被視為氣的聚合離散而成,《易經》遂可被詮釋為一種現象論或是一種精致的唯物論。由《易經》導出的哲學也常被貼上“唯物論”的標簽,張載曾如是被詮釋,王夫之也獲得了如是的待遇。
但是,如據我們上述所列三組條目以觀,張載、王夫之兩人無疑地都在道—器、神—氣、生命—神化、性—生兩兩之間劃下一道紅線,前者都是高一層,並且主宰后者。第一組的張載將“氣”和“形而上”連結在一路,乃因依張載的用語習慣,“神”、“氣”兩字的意義常混用。普通而言,“神”字多指本體之妙用,此義天然是從《易經》“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之義而來,“神”、“氣”相對而言時,其位置是“神”高“氣”低。但是,張載論形上學問題時,“氣”多帶有兼體無累的形上義,其義與“神”同,兩者并沒有區別。第二組王夫之用“掌管神化”之語也值得留意,因為這是王夫之的慣用語,它用以指涉超出者的主宰感化[34]。
更主要的,張載、王夫之明確指出這些形上物的永恒性質:不成毀,亙存亡如此,張載甚至用了“不逝世之物”這樣的描述詞。在現象界者,焉有不成毀或超脫存亡者?理學傳統較少觸及超出的天道生命之生死問題,理學家甚至以關不關心人的逝世亡問題作為儒佛兩教區別的標準。反過來說,理學文獻中少數言及“不朽”、“不逝世”之語者,可以確定地,這些語詞都指向了理學天道生命說的玄奧義,都指向了不成思議的超出層。如只就內容而論,我們將這三條資料劃歸為程朱所言,也說得過往。張載、王夫之的哲學基礎上持的還是理學家超出論的天道生命相貫通的立場,上述三組條目都是決定性的語言,都是《易經》、張載、王夫之思惟中指導性的概念,無從閃躲。但張載、王夫之都從超出論的觀點界定之,沒有一條破例。
我們最后且再以一則同樣有決定性的話語作為分判張載與王夫之哲學的依據。《易·系辭上》有“神無方而易無體”之說,由于本體的堅持是理學家思惟極主要的標志,不論本體的依據是放在心上或在理上思慮,程、朱、陸、王都信任世界有個非經驗性質的底據,此底據是活動的,它是價值之源,要經由意識深層的轉化而顯。但是,《易經》明言“易無體”,“無體而變化無常的世界整體圖像”如放在現象論的氣化風行的觀點下解釋,這種整體存在界可說便是同質的氣運的流宕衍化罷了。沒有衝破,是以,也就沒有興趣義的開顯。《易經》甜心花園的“內在一元性”之說似可成立,漢儒懂得的《易經》的世界觀大要就屬于這種氣化一元論的類型。理學家明顯地不會贊成漢儒的觀點,他們只能堅持《易經》的“無體”之說當另作他解,它不成能違背理學家對“本體”的堅決確定。
關于此句該若何解,在當代新儒家內部曾出現過爭議。有關熊十力與張東蓀的“體用論”之爭相當有名,筆者也行文討論過[35]。此處權且不論,筆者僅在此舉熊十力與唐君毅兩師長教師的說法為例,以作為王夫之公案的參考佈景。唐師長教師早年解此句時,力主中國前賢的宇宙觀是無體觀,《易經·系辭傳》可作見證。此解一出,群賢贊嘆,熊十力見之,獨不以為然。熊十力一貫認為《易經》的立場是于風行中見本體,于變易中見不易,沒有超絕的本體,但不是沒有本體,本體的超出義仍屬畢竟義。唐師長教師當時無法贊同熊十力之說,辯稱道:即此變化風行的總合之自己即為不變,“變之為變之理,即變化風行之現象自己之本體,故即體即用”如此[36]。唐師長教師的意思是說,傳統所說的本體乃是一種對待“變化的總體”的后設語詞,體是用的述詞,就像王廷相、吳廷翰這些天然主義唯包養價格ptt氣論者主張的理是氣的述詞,它是掛搭在氣此實質上的次序或條理之性情。《易經》的“本體”一詞是虛義,它實際指涉的是有次序的變化之整體。后來慧隨歲增,知與年長,唐師長教師乃知熊師長教師當年之說絕不成易。
筆者所以舉熊十力為例,乃因熊十力是王夫之之后,闡釋《易經》義理以及體用論學說最淋漓盡致的哲學家,他的論點不克不及輕易放過。我們且回過頭來,聚焦于體用論的思慮,我們還是以張載及王夫之為例,觀看道體論愚人若何思慮本體的概念。熊十力的觀點其實早見之于張載的著作中,張載在《正蒙》一書快結束處,有言道: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包養價格無體。偏滯于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辟”,又曰“通乎晝夜”。語其奉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而異名爾。[37]
《正蒙》不是《易經》注疏體的作品,但內容多發揮《易經》年夜義,引文明顯地是發揮“神無方而易無體”一說的內涵。張載在文中所說的“體”乃本體之義,它與“神”、“道”、“易”同物異名。“同物異名”若何解,權且不論,但依張載的哲學用語,這些詞匯是天道說的語匯,客觀面的用法,這個慷慨向應該是無爭議的。
我們如比較張載此處所說的“兼體而無累”與張東蓀及早年唐君毅所說,不難發現張載始終堅持“一故神,兩故化”、“兩不立則一不成見,一不成見則兩之用息”,張載的本體永遠脫離不了“一在二的結構之中”之義,但它總是“兼體”而又不限于立體的結構,而是位處存有次序上的超出層。王夫之論理、論本體的“掌管”義,專心分歧。道體論者特別重視體與用的詭譎之“即”的關系,從張載到王夫之,莫不這般。
張載易受誤解,王夫之的本體觀遭到的誤解尤年夜,兩人被誤解的形式是分歧的。我們且看王夫之若何懂得“神無方而易無體”這句話:
“無方”者,無方而非其方,“無體”者,無體而非其體,不據以為方、體也。吉兇之數,成物之功,晝夜之道,皆六合已然之跡,無方者也。而所以變化屈伸,“知年夜始”而“作成物”者,其神也;絪緼之和,肇有于無,而無方之不可者也。易之陰陽六位,有體者也。而錯綜參伍,新聞盈虛,則無心成化,周流六虛,無體之不立者也。[38]
無方、無體之說意指神不拘于“方”,易不拘于“體”,用禪宗的語言表達,也就是“說是一物即不中”之意。此句的意思不是說以無為方體,萬物常處于“化”之中而無貞定之道可言,這種解釋的“方”、“體”成了附搭在氣化之流之上的屬性或規律之意。“氣化無體”之說用以解釋郭象“物自生”之說很恰當,用以解釋早年唐君毅“風行變化自己便是本體”之說也很恰當,但不克不及用以定位《易傳》。王夫之很明確地宣稱:必須向上翻一層,觀其“所以”,乃知神體的無方之不可,無體之不立。明顯地,王夫之的思慮還是體用一如的思慮方法,“所以”一詞是典範的程朱學語言,王夫之應用這個詞語當然不成能不了解它傳達的訊息,但王夫之還是年夜慷慨方地應用了。無方無體與方體是異質的兩層,無方無體指的就是遍乎一切定體之本體之謂也。筆者信任:不論《易經》的旨趣能否真的有張載、周敦頤、王夫之等人解釋的那般明確的承體升引的訊息,但這些道體論的理學家的詮釋只能是超出論的進路,並且熊十力的觀點是可以獲得張載、王夫之等人的首肯的。
四、是生:“固有且同有”的創生
道體論者的著作中似乎存在著兩種分歧的形上—形下(或道—器、體—用)的觀點,就第二節所述,形上的道、理、性依托在形下的事、物、氣下面,形上不單沒有決定形下的存在,它反而因形下事物的發展才得以找到寄身之地,形上的語匯是形下實質的述詞,這是唯物論的解釋。假如依據第三節所說,順序剛好倒過來,道體論者還是認為“道”無形上意義,與“道”同格的“太極”、“神”、“天”也有同樣的形上意義,它的性情與形或形下的“事”、“物”、“器台灣包養網”分歧,並且具有引導后者的氣力,這是體用論的解釋。由于這種兩歧的解釋,我們且再以王夫之的案例略進一解。他同樣注解《周易·系辭上》“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一語,我們已看過“無其器則無其道”這種被稱作唯物論觀點的解讀,但王夫之在另一本書里卻仿若年夜翻其案,他這般解道:
“形而上”者,當其未形而隱然有不成逾之天則,天以之化,而人以為心之感化,形之所自生,隱而未見者也。及其形之既成而形可見,形之所可用以效其當然之能者,如車之所以可載、器包養網車馬費之所以可盛,甚至父子之有孝慈、君臣之有忠禮,皆隱于形之中而不顯。二者則所謂當然之道也,形而上者也。“形而下”,即形之已成乎物而可見可循者也。形而上之道隱矣,乃必有其形,而后前乎所以成之者之良能著,后乎所以用之者之功能定,故謂之“形而上”,而不離乎形。[39]
王夫之說有兩種當然之道,一是“未形”而有的當然之則,一是事物已形之后,能使事物運作者,這兩種當然之道清明白楚,都是“形而上”者。兩種當然之道的表現分歧,乃因“形”之成形與否、時機分歧所致,若語其實,畢竟只要一種形上之道罷了。這一段出自《周易內傳》的注語和第三節援用到的《周易外傳》之注語,都是注解統一段經文,結果兩說不單重點分歧,從概況看來,連內容都有能夠相往懸殊,甚至剛好顛倒,《周易內傳》沖撞了《周易外傳》。《周易內傳》這段注語明顯地把“形而上—形而下”的關系解成“體—用”的關系,而“體—用”的關系則解成“隱—顯”的關系。
“隱—顯”的關系也叫“幽明”的關系,假如我們用“隱顯”或“幽明”來解釋形上與形下的關系,形上為隱,形下(實即“形”)為顯;換言之,本體為隱,世界為顯。那么,這樣的一種形上—形下論,和我們懂得的形上學上的宇宙論之創生有何兩樣?假如我們有兩重世界的意識,不論兩重世界的論述是真兩重,如柏拉圖哲學便是;或是變幻的兩重,如釋教的世界觀;或是詭譎的兩重,如羅整庵哲學;“兩重”一詞總預設了作為本源的形上與形下有種特別的關連。連接兩重世界最常見的概念便是“生”字,亦即由形上者創生形下者,《老子》所謂“道生一,平生二,二生三”;《列子》所謂“有太易,有太始,有太初,有太素”;《淮南子·地理訓》所謂“道始于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皆是。《易經》所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組詞語是更著名的“生”之論述。上述這些名言構成了中國創生論的論述傳統,《易經》一書的貢獻似乎更為嚴重,但王夫之剛好在《易經》這段著名的話語上年夜翻文章,他看到了分歧的“生”。
“生”來自生物學的事實,凡生物總是被生,生物凡是也有生的才能。在宇宙論上的意義,愚人也借了“生”的隱喻。道生萬物,就像怙恃生子。老子哲學就大批運用了母子的意象,以喻道─物之間的關系,他的道是“玄牝”,一位無形無象的年夜母神。王夫之反對這種解釋,他說道:
生者,非所生者為子,生之者為父之謂使然。則有有太極無兩儀,有兩儀無四象,有四象無八卦之日矣。生者,于上發生也,如人面熟耳、目、口、鼻,天然賅具,分而言之,謂之生耳。……要而言之,太極即兩儀,兩儀即四象,四象即八卦,猶人面即線人口鼻。[40]
“于上發生”這個詞語新穎而怪異,其時恍若什么都沒發生。王夫之所以應用了包養網ppt這種荒誕之風的表達方法,應當是傳統的語言不不難表達他想要傳遞的內容,所以他才會自鑄偉詞。他的偉詞意指:所謂所生者與生者的關系并不是母子類型的生物學創生形式,而是兩者一路呈顯,太極之于兩儀、四象、八卦,猶臉面之于線人鼻口之總和。王夫之的比方很像萊爾(G. Ryle)所說的錯置范疇的謬誤,我們要找劍橋年夜學,所以到劍橋年夜學里一棟棟的建筑物里問:劍橋年夜學安在?我們怎能問出個所以然來。年夜學不在一棟棟的建筑物,而是整體之稱謂[41]。太極和世界的關系也是這般,脫離了世界內的事事物物,沒有太極可言。
但是,太極與兩儀、四象、八卦、萬物的關系,如“人面即口鼻”,此比方頗生動,但也無限制。如實說來,人面是口、鼻、眼等感官的總合,但太極之于萬物,并非是萬物的總合,而是于逐一之物上,皆顯太極之整體。王夫之這種思慮方法我們不會太生疏,它是道體論者廣泛性的思慮方法。並且,我們在華嚴宗的“一多相容并立門”;朱子哲學中的“月印萬川”說;甚至于在廣義的泛神論(p包養一個月價錢antheism)或許萬有在神論(panentheism)傳統中,都可看到道與世界不即不離,能產的天然(natura naturans)即所產的天然(natura naturata)之說[42]。
在廣義的道體論(或泛神論)的傳統中,作為最高存有的道(理、太極、天)與世界的關系若何解釋,變得很奧秘。不論若何解釋,有一點相當明白,道體論者拋棄了自無而有、自一而多的“自X而Y”語式的宇宙天生論的思慮方法。普通常認為張載、王夫之等道體論者的哲學是氣論,他們的哲學帶有濃厚的線性發展宇宙開辟論的原因。假如善加懂得,上述這種通說也不克不及說錯,道體論者確實具有線性的歷史發展之意識,道是在氣化歷程中展開,事務的意義只能在氣化全部旅程的脈絡中才可獲得正確的懂得。但線性的歷史發展與線性的宇宙開辟紛歧樣,道體論者無疑田主張道之于物,并非始無后有的創造,也非物外之道的創造,而是無始以來的吊詭同體的感化。王夫之有關宇宙論或氣論的論點,事實上并沒有太被善加懂得,這種忽視形成了包養網評價懂得王夫之思惟的盲點。
我們還是借著後面《周易稗疏》的引文再進一解,以強化非時間性的、非外加的創造之義。王夫之在別的一本注解《易經》的書中提到太極與兩儀、四象的關系有言:
“《易》有太極”,固有之也,同有之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有之則生,同有之則具生矣,故曰“是生”。“是生”者,立于此而生,非待推于彼而生之……所自生者肇生,所已生者成所生……固合兩儀、四象、八卦而為太極。其非別有一太極,以為儀、象、卦、爻之父明矣。[43]
王夫之這段話應當是他論宇宙天生很主要的一段話語,這段話雖然并沒有遭到疏忽,但似乎該獲得更充足的懂得,他在此提出了“是生”的天生形式,個中內蘊可發覆者尚不少。
“太極”天然是形上者,“兩儀”、“四象”、“八卦”則常被規定為形下者,王夫之說:他們彼此的關系是固有、同有,也就是沒有日常語義中天生與被天生,或是先后、有無的關系。兩者同在,事實就是如如地共在,沒有“從彼而生”的關系。王夫之的解釋令我們聯想到郭象的“物自生”說,事實上,假如不論“物自生”背后的哲學理據,就概況價值而論,王夫之的“固有”、“同有”、“立于此而生”似乎意味著儒家版的“物自生”說。但兩者義理結構分歧,不成依郭象義起解。事實上,王夫之版的“物自生”仍須依賴“本體”概念才可成立,沒有郭象說的無因天然的“自生”義。王夫之短促的話語也令我們聯想到明儒的“當下”說,“形上”即于當下的形下事物見之,不待推演[44]。但明儒論及“當下”之語時,常是從主體的當機立斷的直覺效能著眼,他們說的不是“道與世界”的關系。
關于“道與世界”在本體論意義上的關系,王夫之強調的乃為“是生”一語,概況上看來,語義不甚明白,不知他何故能從“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的“是生”高文文章。在《易經》注疏史上,我們似乎極少看到哪位詮釋者曾對此詞匯青睞有加。但是,王夫之是位玄思才能極強的愚人,也是語感很強的詮釋者。他的詮釋有獨特的風格,他一貫很重視語義的表達方法,其進路骎骎然有乾嘉學者戴、段、二王之風[45]。他指“是生”一詞值得留意,這是種急辭,他的論點受張載影響。張載曾說:論及形上真諦時,緩辭缺乏以盡之,“緩辭”大要指波折的辨析方法,所謂的discursive。表達玄理,需用“急辭”。王夫之注經,也很重視語氣,他認為緩辭缺乏以窮盡玄思的內涵,也只能應用“急辭”,包養故事“急辭”大要表現語意的返身自我指涉,它要撤消失落主詞(太極)與賓詞(兩儀)之間的距離。“急辭”和“當下”的思維方法相關,它顯現了主體判斷的直接性,但王夫之的“急辭”不是心學意義的,而是本體論意義的。
王夫之反宇宙開辟論的思慮方法,是他的哲學的一年夜特點,我們且再舉他注《莊》的一例,以作補充。《莊子》提過對于宇宙與萬物關系甜心寶貝包養網的幾種思慮,此中有人名曰季真,提“莫為”之說,有“接子”其人則說“或使”之論。“莫為”類似于“無因天然”說,“或使”則持“主宰”說。對于這兩說,莊子假書中人物至公調之口說:雞鳴狗吠,沒有人了解它們何故這般,也不克不及清楚它們有何意圖。他進而斷言道:“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于慷慨。”《則陽》這段話論及萬物的存在有沒有創造者,理論價值極高。王夫之于此有注:
言或使,則雖不得其主名,而謂之或然,而終疑有使之者,則猶有所起之說。此說最陋,故郭象氏以季真之莫為為是,而實否則。莫為、或使,之二說皆是也,皆非也。皆非故皆是,皆是則是其所是,而固皆非矣。夫言或使者,如轂之有軸,磨之有臍,為天之樞,道之管,而非也。道一環也。環中虛,虛不克不及使實也。言莫為者,如環中之虛,而既有環矣。環者,物之著名實可紀、精可志者也。有實而無處,而初非無實也。之二說者,皆未得環中之妙以應無窮,而疑虛疑實,故皆非也。[46]
《莊子·則陽》篇的話語值得留心,王夫之這段注語也很值得留心。莊子對季真與接子的批評不是偶爾的,我們在《天運》篇即看到莊子對于宇宙的運行畢竟是有興趣行之,抑或無意行之,曾發出有名的感嘆。王夫之的注解借莊子喜用的渾圓隱喻,如輪軸、石磨、環中為例,指出渾圓之動不是沒有推動者,郭象支撐“莫為”說,主張物自生,這種懂得是錯誤的。但沒有定點,并非沒有現實存在以外的氣力,所謂“有實而無處”,所以找不到推動者。莊子論道的運動有“外化而內不化”之說,這個“內不化”的點是《莊子》書中極年夜的奧秘,因為氣化的世界觀中沒有“內不化”的定點。但或許也不是那么奧秘,這個無處之點其實散布于環的每一點。王夫之的注解合適莊子之說,他既反對無因天然之說,也反對活著界之上或之外尋求超絕的推動氣力[47]。
王夫之的形上學之特別,他之反線性的宇宙論之立場,我們還可從他對《序卦傳》的不滿看出。眾所共知,王夫之平生拜伏《易經》,但因為反對劣義的宇宙開辟論,他竟不吝與《易經》經文決裂。《序卦傳》有言“有六合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王夫之很反對“然后”的提法,他說:
道生于有,備于年夜,繁有皆實,而速行不息,太極之函乎五行二殊,當然如此也。有所待非道也,續有時則斷有際,續其斷者必他有主,陰陽之外無主也……《序傳》曰:“有六合,然后萬物生焉。”則未有萬物之前,先有六合,以留而以待也。[48]
王夫之說的“生于有”一詞的“生”是虛說,并非“有”生“道”,而是意指道即當下,不成逆溯至與世界隔絕的“空”或“無”,此義乾元的“年夜生”庶幾近之;“備于年夜”意指道內在于萬物,不用外求,此義坤元的“廣生”庶幾近之;“繁有皆實”意指年夜生、廣生者皆是本體論意義的真實。我們對這些語言應當不會太生疏,王夫之反“有六合然后有萬物”之說,乃是為道體論的創生爭位置,也可以說為廣義的泛神論的創素性爭位置。在泛神論的世界里,沒有“然后”的空間,因為有“然后”即意味著有斷隙,有銜接,有外于天然的推動者。王夫之斷言:陰陽之外固無主也。我們可以依王夫之的哲學對他的斷語再下一轉語:太極即內在于陰陽之能產的陰陽,即內在于四象之內的能產的四象,即內在于八卦內的能產的八卦,即內在于天然之內的能產的天然。《序卦》所說乃謬誤之語,王夫之因此斷言:《序卦》不是圣人所作。王夫之的道─物關系乃“是生”關系,“是”者,此也,“是”乃不容再有剖析的能夠性的當下,“是生”結構的道—物不是天生者與被天生者;是同時具足,而不是“然后”的時間性事務,但也不是“所以然”的靜態存有論的事務。
當代新儒家論《中庸》、《易經》或北宋周敦頤、張載之學時,有“本體宇宙論”之目。依西洋哲學的分類,本體論與宇宙論屬“形上學”名下的分歧兩目,宇宙論言變化,本體論言依據。中國的儒道形上學之本體常被認為永恒的作動者,不是靜態的依據意,它的創生是發生于時間之內的非時間性事務,是形于個體之內的非個體性事務,新儒家以“本體宇宙論”之名稱呼“是生”的創造論,《易經》以“流形”稱呼“是生”創造的個體[49]。我們現在透過王夫之的注解,對“本體宇宙論”及“流形”諸詞的特點,或許更可從頭貞定。
五、同時具足圓缺門
道體論的本體概念強調形下、器、用的主要價值,在語言情勢上,比起形上、道、體的觀念來,我們甚至可看到形下、器、用等概念的“首出”的優勢地位,但它的哲學形式明顯的不是唯物論,也不是唯心論。道體論的主體與功用,或許說太極與萬物,其關系乃是“固有且同有”,這種關系顯示兩者的關系不是工匠(道)與創造品(器)的關系,不是騎士(道)騎馬(器)的類型,也不是車夫(道)上坡推車(器)的形式,總而言之,兩者不是本體與個體之間的內在關系,而是詭譎的內在共構為一的關系。就情勢看,它也可以說是種廣義的泛神論的類型。
泛神論由于主張“神”與天然的統一或合一,是以,泛神論與唯物論的分際很不難含混。因為既然為“一”,中間沒有差別,所以說此總體為“物”,或說此總體為“神”,皆可成立,因為“神”與“世界”不分。不論在中國或在東方,泛神論類型的哲學家的哲學性質都很難定位,他們常被置于唯物論或徹底的神性論的兩極下作解,斯賓諾莎、布魯諾究竟是唯物論者或是陶醉于天主的人?眾人一向有爭議。張載、羅欽順的哲學究竟是天然主義的唯物論?還是小年夜精粗無不在的體用論?中國哲學史學界的爭議之聲也始終不曾停歇。
但是,假如泛神論一詞可以成立,也就是“神”這個概念假如有獨立的意義的話,為防止“神”與“天然”完整統一導致兩詞的排列再也沒有興趣義,出脫逆境之計,生怕不克不及不在統一中顯示出差異。學者采取的戰略或強調“神與天然的統一”與“神與天然的差異”兩說同時成立,悖論是終極者的本質,天主是雙面夏娃,這是種悖論式的提法,冥契者多有此類敘述[50]。要否則,就是認為兩者在統一中幾多仍保存有神之盈余的意義,泛神論的“神與天然統一”比普通的統一關系多出不成思議的意義成分,這是萬有在神論(panentheism)的提法,黑格爾哲學可以這般被解釋[51],耶教的冥契論者也會被歸宗于此種類型,如于中國考古事業有功的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神父亦可被這般解釋。
學者不論是采悖論式之說,或是采萬有在神論之說,雖然都給形上者保存了此世總體之外的獨特地義,但仍與王夫之所代表的道體論者所說者分歧。上述兩說皆無法解釋王夫之的有名命題:何故先有其器才有其道?我們在第二節引他在《周易外傳》所說的“無形而后無形之上”,該怎台灣包養網么解釋?不單這般,也無法解釋,何故新興事物還會產生新的道,也就是豐富本體原來沒有的內涵?王夫之說,世界在永恒地進行當中,只要某物出現了,其物之道才會出現。王夫之這個說法不單顛覆了傳統泛神論的主張,更完整翻轉了萬有神論的神—萬物之關系,也顯然和他論體用關系時的隱顯之說紛歧樣。因為“隱顯說”意味著顯者只是隱者的呈現罷了,兩者表里如一,表(顯)者并沒有比里(隱)者多出任何內容。泛神論的顯—隱關系可以說是套套邏輯,只是這種套套邏輯乃是形上學意義而非知識論意義的。一切后續的發展皆已先驗地見于道體之中,宇宙的發展是依據劇本表演的神圣喜劇。
道體論的道器說顯然充滿了牴觸的內涵,因為按照傳統儒道兩家對本體的懂得,本體的性質常被設想貫通始末,總攬萬有,是“一法界年夜總相法門體”,《年夜乘起信論》的解釋雖依佛典立論,卻可作為共法。世間萬物的天生可說一切由此法界流,一切還歸此法界。但是,王夫之論形上—形下、道—器諸論,明顯地說表者(顯者)不單比里者(隱者)多出了內容,這種多還不是數量意義的多,而是質的差異之多。因為有器包養軟體才有道,意思也就是器生出了道。道既涵器,器又反饋道。本體要在形下器物出現于世時,其某種意義下的道之內涵才可呈顯出來,本體有待于器物。
本體總是被視為圓滿具足的,王夫之的本體觀特別分歧,因為他的本體中有歷史的意識。人的世界乃是歷史的世界,歷史世界中的事物總是新新不窮地興起,事前無法揣測。所以本體不克不及不處在永恒的吸納新興事物的道(理)之過程中,本體的部門內涵是要由新興器物替它補充的。本體在本質上即處于完善與盼望,但“本體”的概念卻又意味著完備具足,所以更正確地說:它總是既完備又完善,既滿足又盼望。道對器何故處于既含攝又被補充的地位?顯然,新興的事物有道之在其自體的本體所沒有的性質,道器關系是“道生器,器生道”的互涵的結構。
王夫之道器論的語言既表現道生器,它乃非時間性的隱—顯的關系;也表現器生道,它表現了道器是在時間中的突變式的成長關系。兩義牴觸,但同時證成。筆者所謂的“突變式的成長關系”有特別的指謂,因為器由道長成,這是理學體用論的基礎規定。道假如是本體的意義,則道作為“母體”的意義即無法改變。但依王夫之義,我們可以推論說等器成長成熟后,即會產生類似突創進化論所說的突變,其性質不是原來的結構所能解釋的。或許我們不用帶進突創進化論的概念,因為器氣相連,《易經》說:時之義年夜矣哉!世間事物隨時都會產生新的性質,新的性質豐富了原有的道之內涵,因此也有新的道產生。器所以有此特徵,乃因器是氣化之物,物相是氣的暫凝狀態,物是“流形”,它是實質便是名實相符之“物化”。氣化恒處于時間的流變當中,時間是打破統一性的利器。所以說道生器固有理路,說是器生道,一樣也有足以成說之處。道是無待與有待的統一,是圓滿與完善的同時具足。
按照王夫之的學問旨歸,道同時具足圓滿與完善,他的本體論思惟的特別正在此處。在傳統體用論的思慮中,“用”總是由“體”發出的,“用”極其至,仍只是“體”此玻璃底片的相片,它的價值早已存在于底片中。即便禪宗、王學那么強調即體而言體在用,即用而言用在體,用的價值仍只是體的具體化原則罷了。王夫之否則,作為形下的事物之超出源頭雖然在體,但事物一旦出現,它即在時間中,它即依氣化日新日成,它即有原有結構不曾有之新義,這個新義會長出超出的道體沒有的內涵,依據體用論的原則,此長出者又將為形上所接收,成為新的固有,因此成為它的內涵。
在前文論及太極—兩儀的關系時,王夫之說:太極與萬物是固有且共有。王夫之不是反對太極的“生”之概念,而是他的“生”便是“有”。太極從來不會先于六合,也不會后于六合,它們是固有且共有的關系,本體抹殺了時間。但是,“固有且共有”只是故事的一面,因為一旦固有且共有,太極即以物的面孔顯現,它即處在時間的流變中,流變帶來決裂,決裂會帶來本來的太極所未有新事物,新事物即有新理,此新理的內涵又將為形上之道所接收,形下之物回饋了形上之道。在王夫之的思惟中,形上之道既是一切圓滿,但又是一切在發展的,也就是它具有原初的性質,但也有后得的性質。形上之道會發展,它有些內涵要靜候形下之器物的回饋才擁有,這樣的論述頗為詭異。關鍵在王夫之的道的吊詭性,它既在時間之外,但同時也處在時間變化的氣化之流中,時間是形而上之道不成或缺的實現原則。因為只要在時間的變化中,才會帶出道原來沒有的新理,這種新理是道的后得義。
王夫之形上學最年夜的特點不在形上—形下的“固有且共有”,而在兩者的相待而生,互補互涵。互補互涵一詞意味著:(一)只需無形,即無形而上,形的意義有“幽”、“潛”、“隱”的形上向度孕育其間。(二)只需無形,即進進氣化歷程,時間、變動帶進來,即會產生原來的形上界沒有的內涵。(三)“形”與“形而上”不單在存在論上不成分,就概念自己來看,兩者在本體論意義上也不成分,兩者彼此補足,才算完全。他的這個理念有多重的臉孔,在分歧的場合,王夫之分別提過“理氣互涵”、“形器互涵”、“道器相涵”等,千面一面,其本源的洞見在于道的時間性與非時間性的吊詭統一。
假如我們要清楚道既是圓滿但又是在發展中的思惟,從道落實于人道的結構中來談,議題的面孔可以更明白。王夫之的人道論的一年夜特點在其“日誕辰成”之說,這是研討王夫之哲學的學者幾乎都會留意到的議題。這種“日誕辰成”的人道論強調人道在發展中會創造出新的價值,有關“日誕辰成”說的解釋有多種,筆者認為此“日誕辰成”說能夠采取經驗論的解說,這般解說能夠應用的是種子式的隱喻,亦即人道由種子般的原初狀態漸漸長成。此固一說,但種子說的隱喻無法解釋“新的理”若何被創造出來。“日誕辰成”說也不克不及采取心理學的解釋,亦即人的體質有天然成長的趨勢,因為這種解釋不需求將體質以外的“道”的原因帶進來。王夫之畢竟是理學家,經驗論的解讀是不如理的。
如前所述,王夫之信任後天的性善論,就概念而言,性善與人格典范的圣人是如如映照的關系。王夫之無疑地不信任“復性說”,從李翱以下所提出的“復性說”皆主張學者的盡力是要回到原初的人道之善,程朱陸王在此皆無異議。王夫之信任有一超出的人道之善,但功夫論的關懷不在永恒的回歸。王夫之信任人的明智處在不斷變化的世界當中,它可認識新理,同時,認識者本身的人格也可成長,新理成為人格的成分。是以,格物窮理所得者不單不用是性善論的善性原有的內涵,並且,還可以補足它,王夫之的人道論預設了本體與功夫的互涵。“智”在王夫之哲學中的地位和朱子的智之地位比擬,值得進一個步驟究查。
王夫之“形上—形下互涵”的命題在其歷史哲學中再度明顯地表現出來,王夫之看歷史,歷史是有目標的,是天(道、理)此超出者在人類歷史中起感化。有超出界參與此中的歷史不成能沒有向善此目標趨向的感化,但歷史事實明顯地常與感性的預期相反,司馬遷《伯夷叔齊列傳》感嘆天意之有無,這是個極鮮明的案例。王夫之論歷史,認為歷史的目標法則有時需透過私家的、欲看的、非感性的前言,才可顯現出來。好漢人物的行為常是不品德的,但正因為不品德,他反而是以無意中成為天意的東西,感性在歷史的表現不是直線的。王夫之論秦始皇的功過時有“天假其私以行其至公”之論[52],以調和歷史判斷與品德判斷的差距。司馬遷假伯夷、叔齊事跡,嘆天道之迷茫,正義之滄桑。王夫之很反對司馬遷對天意的懷疑,他認為天意從來不直接對當事人或當時人揭開面紗[53]。
王夫之的歷史是品德的歷史,是感性的歷史,作為價值來源的天要在歷史的過程中顯現天意。但天意不直接顯現,相反的,天要在一段歷程之后,因新的局勢出現,其原初的意義才可顯現出來。亦即歷史上的新理需求新的“勢”構成后,才可呈現。換句話說,歷史假如沒有發展到新的階段,有些主要的歷史事務之意義是無法知曉的,包括天、道在內都無從事前猜測,天道反而需求歷史的發展才幹補足這個存有次序的缺口。天(道)是價值的源頭,歷史是在時間之流中顯現的事務,體用相待即意指天意與歷史是互涵的。
王夫之哲學的整體論性情很強,前輩學者常以王夫包養網心得之比擬黑格爾,筆者認為這種類比相當有事理,遠比唯物論形式的解釋貼切並且深入。在整體論思慮形式下,形上—形下互涵的形式會月印萬川式地顯現出來。但筆者信任,王夫之的道器相涵的內涵更復雜,它超越了泛神論或萬有在神論的藩籬。它的來源當是來自于《易經》的結構,當圣人并舉乾、坤,而最后殿之以既濟、未濟時,我們看到一種特別的世界結構,作為根源的太極以相偶的情勢出現,此即乾元、坤元之構造。而世界不克不及沒有一終極的目標,以作為世界法庭的見證。但世界既然是世界,它就有歷史的架構,就不成能有終極的定點,如如不動,所以“既濟”之后需求有“未濟”。永恒總是在變化之中,本體總要等候感化的不斷補足。王夫之透過《易經》呈現道的整體性、歷程性之特點,也就是道詭譎地同時具備圓滿與創新。
六、結論:“體用相待”的辯證法
道作為全國萬物的存有原則,全國雷行,物與無妄,此義被忽視久矣!作為理學第三系的道體論應時現身,是其時矣!
假如我們從理學各系統出現于歷史的時間判斷,作為理學第三系的道體論其實該視為理學第一系,因為理學在十一世紀出現于北宋的歷史舞臺時,道體論是第一支具有思惟特點的理學隊伍。從周敦頤、邵雍到張載、程顥,他們當時面對的時代課題就是若何回應釋教的挑戰,釋教當然關心人的安居樂業的問題,存亡事年夜,焉能沒有主體的關懷。但我們不要忘失落,釋教同樣對一切法有存有論的解釋,而它的存有論的解釋即樹立在緣起性空的基礎上。對自我真實的尋求和對天然真實的尋求是一體的兩面,釋教有釋教的關懷,儒家有儒家的承諾,這是北宋理學興起的佈景。
理學的興起預設了與佛老(尤其是釋教)教義的對勘,對比、對抗。北宋理學興起的一年夜事因緣可以說是以天道觀對應緣起性空觀,北宋理學家從《易經》、《中庸》獲得本體宇宙論的思慮方法,它從“天”的基礎上,思慮萬物存有的問題。我們假如將北宋理學家思慮的方法和主張“格物窮理”的性體論,或和主張“致知己”的心體論作一對照,即可發現從“天”的立場出發和從功夫論的立場出發,其思慮會有相當的分歧。前者有全體世界的思慮,主客并重。北宋理學“本天”的思慮乍看之下,類似漢唐天人感應的哲學。但是,漢唐儒者之“本天”并沒有北宋理學家視天為本體的那個向度。
北宋理學的“本天”之“天”在以往的歷史上可作“萬物總稱”或“天然”義解,由此一轉,“天”可所以整體天然的稱呼。尤其在中國文明的傳統中,“天”常以“氣化的總體”之臉孔出現于世,天然氣化,天生萬物,這是天然哲學的談法,其“氣”有精微的物質之義。道體論者確實是重氣的,他們比不少所謂氣論的哲學家還要重視氣的效能。但是,他們的氣論不是王廷相系統下的那種以天然主義宇宙論為中間的類型,而是超出型的道論,或許說廣義的泛神論的類型,筆者稱之為後天型的氣論。後天型的氣論和后天型的氣論在語言敘述上不難混雜,但只需是後天型的氣論,它的思惟的形態幾乎都是體用論型的,後天義的“氣”乃是體用論的“用”字。道體論者的氣論是體用論的氣論,他們的“氣”也是體用論的“用”字的意義,道體論者的體用論近乎泛神論的類型。
道體論的體用論當然可視為泛神論下的一個類型,但泛神論下的形上—形下關系雖說包養違法是一體,但此一體在本體論的構造上常是以體吞噬用,更確切地說,乃是以本體吞噬現象,因為形下之物在本質上仍只是形上之體的顯現,由微隱而彰著,現實只是原來即已存在的構造的外顯,在本質上,“外顯”的現象并沒有增添新的內容。所以黑格爾辯護斯賓諾莎的“天主即天然”之說時說,斯賓諾莎的哲學與其說是無天主論的唯物論,不如說是無物質義的無世界論還來得恰當些。無世界論即意指個體之“個”都撐不住自體,主體之“主”都要融進主客未分之“一”之中。在廣義的泛神論的世界,東方常見的泛心論的體系也可以包含在內,本體(泛神之神、泛心之心)是價值的一切,也是存在的一切,在一切內在性的流動中,個體存在的目標就是向未分化的原點的回歸。
道體論者的體用論卻非這般,他們的形上—形下的結構不是套套邏輯的恒真式構造,而是形上—形下互涵,形上既是完善自足的,但同時也要自行創化的。落在道器論上講,便是道器相涵的形上學,道的內涵有待器來補足;器的內涵,其本質也是流動的,它是“流形”,它需求作為本體的道的支撐。在道—器、體—用、形上—形下之間,概念的本質是自我否認的,並且是要相對概念加以補足的,王夫之的體用論展現了一種特別的“辯證法”。道體論者的形上學不單修改了中國以往各種唯物論型的氣論的哲學,同時也修改了作為主流的泛心論哲學。
“辯證法”當然不是王夫之的用法,而是二十世紀以后出現于中國學界的用語,是外來語。在黑格爾哲學中,辯證法是精力運動的情勢,它連結了無限與無限,它戰勝了否認與確定,它整編了牴觸與一體。在綿延甚長的中國哲學傳統中,王夫之的形上學蘊含特別濃厚的辯證觀點,我們要找到可以與之婚配的思惟家還不不難。反而,在黑格爾處,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思惟色澤,王夫之統一了形上與形下,理與氣,體與用,他一切對經驗世界事項的確定都蘊含了對形上之道的補充。假如我們把他的觀點稍加翻譯,能否可說他的道有“雙重的運動”:“理念永遠在那里區別并分離開統一與差別、主體與客體、無限與無限、靈魂與肉體”,但另一方面,辯證法“使得這些明智的、差異的東西回歸到統一”[54]。上述所說為黑格爾的語言,但我們不難看出王夫之的靈魂。黑格爾與道體論者的哲學定位頗相契,其相契和兩者同樣在一種無限的人道論視野下看到精力運動的情勢有關。
但相對于辯證法預設的統一—分離—牴觸—統一的發展過程,王夫之則認為精力運動的過程不克不及終止于重回原初的統一,而是統一后仍繼之于不斷地分化。因為這是歷史的性質使然,也是人道的歷史性原因使然,但不斷地分化(用)總會補足于完全的原初的本體,只是完全的本體之所以完全,乃因它永遠有完善,它需求在歷史中攤展出的新理之補足。莊子有言,天也者,“參萬歲而一成純”(《齊物論》),王夫之極重視此語,他將莊子的“天”引進他的本體論中,天意(道體的內涵)要走完歷史的過程后才顯現出來,就此而言,黑格爾可說是王夫之的歐洲盟友。但王夫之重視氣、器、形下對理、道、形上的補足,前者同樣有另一類的存有包養平台次序的優越性,因為歷史既屬于天卻又不是天意所能管轄,所以“參萬歲而一成純”的天道法庭永遠開不成,因為歷史無盡頭。
道體論哲學家在當代學界并沒有遭到太多的忽視,此學若何懂得,顯然還年夜有調整的空間。尤其王夫之這種體用相待、道器互涵的性情很特別,超越以往的體用論的思維。所以他雖然是平易近國以來很受重視的哲學家,他是馬克思主義學者眼中的中國哲學的代表,他也是新儒家熊十力、唐君毅諸師長教師常引為同調的先行者。但王夫之這種詭譎的體用相待、道器互補的理論卻沒有遭到他們足夠的青睞,道體論的學術潛能仍待繼續發掘。
注釋:
[1]japan(日本)學者西周最早將ontology漢譯成“理體學”,“理體”也是性理學的語言。見西周《百學連環》(節譯),支出沈國威《嚴復與科學》,南京:鳳凰出書社,2017年,第261頁。至于作為ontology的譯語的“本體論”一詞若何出現,待檢證。
[2]程頤《易傳序》,支出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689頁。
[3]熊十力《講詞》,《十力語要》卷一,上海:上海書店出書社,2007年,第40頁。
[4] 理學除了程朱一系、陸王一系外,能否還有第三系?此問題為理學史的一年夜議題。牟宗三師長教師提出胡五峯、劉宗周一系,亦即“以心著性”系,為第三系最主要的提案者。筆者認為當以本體宇宙論為理論焦點的愚人,北宋的周敦頤、張載、邵雍、程顥以及晚明的方以智、黃宗羲、王夫之當是最主要的代表。參見拙作《重審理學第三系》,支出林月惠編《中國哲學的當代議題:氣與身體》,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討所,2019年,第93—132頁。
[5]龍樹《中論·觀四諦品第二十四》,支出龍樹造,青目釋,吉躲疏《中論、百論、十二門論》,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94年,第61頁。
[6]《老子》第四十章,支出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品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10頁。
[7]湯淺泰雄辨別東、東方形上學之異同,常言及此義。他上世紀末發表《“氣之身體觀”在東亞哲學與科學中的探討》,此文支出拙編《中國現代思惟中的氣論與身體觀》,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3年,第63—99頁。此文當是中文學術界較早引介湯淺泰雄東、東方形上學異同之文章。
[8]《老子》第二章云:“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低相盈,音聲相和,前后相隨。”
[9]脫脫等《宋史》列傳第一八六《道學一》,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第12710頁。
[10]程頤《附師說后》,《河南程氏遺書》,《二程集》卷二十一,第274頁。程頤“圣人本天”的“天”,其意義其實是“理”,程顥的用法更像是張載所說的“由氣化有道之名”。
[11]程顥、程頤《端伯傳師說》,《河南程氏遺書》卷一,《二程集》,第4頁。
[12]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中,《牟宗三師長教師選集》第6冊,臺北:聯經出書事業公司,2003年,第23—92頁。
[13]牟宗三當然曾以唯物論對待王夫之,但也曾為王夫之辯護道:“若通曉程朱陸王之所講,則知船山所言皆不悖于宋明儒之立場。有人把他往下拖,講成唯氣論,實年夜謬誤。”參見《黑格爾與王船山》,《性命的學問》,臺北:三平易近書局,1970年,第178頁。
[14]牟師長教師的緘默或許源于其師熊十力以及其友唐君毅都高度揚譽王夫之,視之為理學發展的岑嶺。他或許因師友之情誼故,很少公開批評王夫之。
[15]以上兩段引文見王包養違法夫之《周易外傳》卷五《系辭上傳第十二章》,支出《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長沙:嶽麓書社,2011年,第1027—1029頁。
[16]孔穎達《周易正義》,李學勤主編,臺北:臺灣古籍出書公司,2001年,第2冊,第344頁。
[17]至于“崇有”、“貴無”之爭,這是另一個玄學內部的問題。
[18]陸象山的反對除了哲學的來由外,還獲得了一項版本學的支撐,因為《太極圖說》的另一版本的第一句作“自無極而為太極”,這個版本多出了“自”、“為”兩字,給朱子增加了許多的困擾。朱子花了不少力氣,批評這個版本帶來的問題。
[19]王夫之《讀四書年夜全說》卷十,《船山全書》第6冊,第1111—1112頁。
[20]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3頁。
[21]程朱理學的必定年夜體借自先秦儒典的“無妄”、“誠”等主要概念,用以表現這種超出的確定。如《易經》所言“全國雷行,物與無妄”,世間無一物是虛幻而生的。或《中庸》所言“誠者,天之道”、“不誠無物”如此。“誠”字不只是人的品德動機之真摯不貳,它更指向了“存在”便是一種價值意義的真實,“成”、“誠”兩字不僅文字上是孳乳的關系,文義上也是相通的。“誠”是品德語匯,也是本體論的語匯,它同時負責“應然”與“實然”。
[22]《河南程氏遺書》卷三,《二程集》,第67頁。
[23]《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五,《二程集》,第162頁。
[24]參見侯外廬等主編《宋明理學史》下冊,北京:國民出書社,1997年,第918—932頁。
[25]王夫之《周易內傳·系辭上傳第五章》,《船山全書》第1冊,第524—525頁。
[26]王夫之《讀四書年夜全說》,《船山全書》第6冊,第994頁。
[27]張載《橫渠易說·系辭上》,支出章錫琛點校《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第207頁。
[28]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卷一《太和篇》,《船山全書》第12冊,第21頁。
[29]張載《經學理窟·義理》,《張載集》,第273頁。
[30]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卷一《太和篇》,《船山全書》第12冊,第23頁。
[31]張載《正蒙·誠明》,《張載集》,第21頁。
[32]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卷三《誠明篇》,《船山全書》第12冊,第128頁。
[33]劉述先《重訪黃宗羲——新版自序》,《黃宗羲心學的定位》,杭州:浙江古籍出書社,2010年,第1頁。
[34]王夫之論“本體”義有言:“《易》固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之一之云者,蓋以言夫掌管而分劑之也。”見《周易外傳》卷五《系辭上傳第五章》,《船山全書》第1冊,第1004頁。“形陰氣陽,陰與陽合,則道得以均和而掌管之。”《周易外傳》卷六《系辭下傳第五章》,《船山全書》第1冊,第1043頁。“其善者,則一陰一陽之道也:為掌管之而不任其情,為分劑之而不極其才。”《周易外傳》卷七《雜卦傳》,《船山全書》第1冊,第1112頁。
[35]參見拙作《近現代儒家思惟史上的體用論》,《新亞學術集刊》第17期(2001年7月),第195—226頁。另參見蔡岳璋《在中國思慮“本體”:以熊十力、張東蓀的對話為線索》,《人文中國學報》(未刊稿)。
[36]唐君毅《中國文明之精力價值》,臺北:正中書局,1965年,第2頁。
[37]張載《正蒙·乾稱》,《張載集》,第65—66頁。
[38]王夫之《周易內傳》卷五《系辭上傳第四章》,《船山全書》第1冊,第523頁。
[39]王夫之《周易內傳》卷五《系辭上傳第十二章》,《船山全書》第1冊,第568頁。
[40]王夫之《周易稗疏·系辭上傳》,《船山全書》第1冊,第789—790頁。
[41]吉爾伯特·萊爾著,徐年夜建譯《心的概念》,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10—11頁。
[42]“能產的天然即所產的天然”之說,中世紀神學家有此論。布魯諾(Giordano Bruno)說:天主即能產的天然,此語亦道地。
[43]王夫之《周易外傳》卷五《系辭上傳第十一章》,《船山全書》第1冊,第1023—1024頁。
[44]東林黨年夜老顧憲成曾撰《當下繹》一文,專論“當下”義,他說:如以本體言,“當下”就是“合下”,亦即通攝過往、現在、未來,“吾性合下具足”。如以呈現言,過往、未來“不成離于見在”。參見顧憲成《當下繹》,《顧文端公遺書》,支出沈善洪主編,夏瑰琦、洪波校點《黃宗羲選集》第8冊,杭州:浙江古籍出書社,1992年,第753頁。
[45]戴震對經典中的“之謂”、“謂之”的差別,曾提出有名的判斷:“前人言辭,‘之謂’、‘謂之’有異:凡曰‘之謂’,以上所稱解下,如《中庸》‘天命之謂性,任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為性、道、教言之,若曰性也者天命之謂也,道也者任性之謂也,教也者修道之謂也;《易》‘一陰一陽之謂道’,則為天道言之,若曰道也者一陰一陽之謂也。凡曰‘謂之’者,以下所稱之名辨上之實,如《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此非為性教言之,以性教區別‘自誠明’、‘自明誠’二者耳。《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本非為道器言之,以道器區別其形而上形而下耳。形謂已成形質,形而上猶曰形以前,形而下猶曰形以后。”參見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卷中·天道》,《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9年,第288頁。但是,王夫之也提過類似的判準:“‘之謂’,彼當然而我授之名也……‘謂之’,我為之名而辨以著也。”《讀四書年夜全說》卷三,《船山全書》第6冊,第538—539頁。王夫之“謂之”、“之謂”的分別當然有能夠遭到程顥“不成移‘謂’字在‘之’字下,此孔子文章”之說的啟發,但王夫之的解說通明多了。戴震不知能否有得于王夫之,但是,兩人思慮經典術語時,其思維形式竟碰巧合如是,由此可見王夫之對文字層面的內涵頗下過功夫。
[46]王夫之《莊子解·雜篇·則陽》,《船山全書》第13冊,第405頁。
[47]我們所以引王夫之的《莊子》注為例,乃因王夫之對莊子的懂得與眾分歧,王夫之雖然沒有暢言莊子儒門說,在許多篇章,也常老莊、道釋聯言,一并批評。但他的《莊子解》確實主張莊子與《庸》、《易》的本質性關聯,兩者言“天”,其理論也頗相涉。
[48]王夫之《周易外傳》卷七《序卦傳》,《船山全書》第1冊,第1091—1092頁。另《河南程氏遺書》卷六程子云“序卦非易之蘊,此分歧道”下有一注語“韓康伯注”,《二程集》,第89頁。卷六所收為“二師長教師語”,不知說者為程顥或程頤。
[49]“流形”此詞語出自《易經·乾卦》:“年夜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二十世紀末,上海博物館公布新收戰國簡帛,中有《凡物流形》一文。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躲戰國楚竹書》,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2年,圖版,見第75—132頁;釋文,見第219—300頁。上博竹簡《凡物流形》公布后,頗遭到學界重視,但“流形”一詞已見于傳世文本《易經》中,可見此詞語在戰國時期曾風行過。“流形”意味著形之流動,流動之形乃是形的本質,流形這個概念是對靜態世界觀的否認,王夫之哲學的精力顯然承自《易經》的傳統。
[50]關于冥契者與悖論的關系,參見史泰司著,拙譯《冥契主義與哲學》,臺北:正中書局,1998年,第341—380頁。
[51]參見辛格(Peter Singer)著,李日章譯《黑格爾》,臺北:聯經出包養價格書事業公司,1984年,第97—98頁。
[52]參見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一,《船山全書》第10冊,第68頁。
[53]參見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七,《船山全書》第10冊,第281—282頁。
[54]黑格爾著,賀麟譯《小邏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403—404頁。
彙整
- 2025 年 9 月
- 2025 年 8 月
- 2025 年 7 月
- 2025 年 6 月
- 2025 年 5 月
- 2025 年 4 月
- 2025 年 3 月
- 2025 年 2 月
- 2025 年 1 月
- 2024 年 12 月
- 2024 年 11 月
- 2024 年 10 月
- 2024 年 9 月
- 2024 年 8 月
- 2024 年 7 月
- 2024 年 6 月
- 2024 年 5 月
- 2024 年 4 月
- 2024 年 3 月
- 2024 年 2 月
- 2024 年 1 月
- 2023 年 12 月
- 2023 年 11 月
- 2023 年 10 月
- 2023 年 9 月
- 2023 年 8 月
- 2021 年 3 月
發佈留言